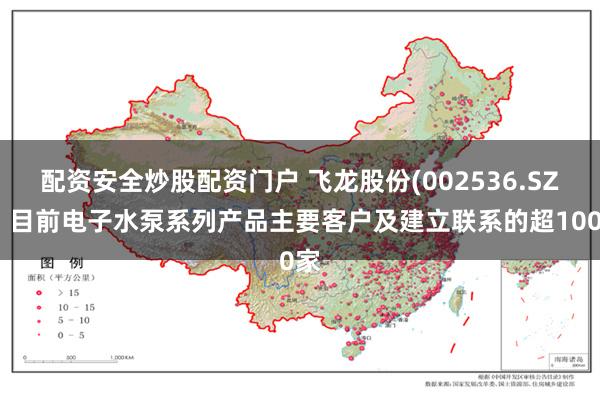康鹭片区,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,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,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。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股票杠杆炒股,被称为广州“最贵旧改”。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,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,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,但直到2023年,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:当年年底项目首拆,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。
素材/赵志勇(整理:白叔)
声明:故事来源生活,为了阅读体验,情节略微改动,请勿过分解读。
1983年,这是我在新疆当兵的第二年,记得在一个炎热的下午,连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,他说如今正是抢收麦子的季节,我们作为军人,应该为当地老乡做些什么。
连长话音刚落,指导员随即布置任务,由带他亲自带队,在连队中抽出一个排的战士去帮助老乡收割麦子,其中有我一个。
在帮助老乡割麦子时,我们这些战友没有一个偷奸耍滑的,就像给自己家里干活一样。我们帮老乡干了三天半,农活干完,我们这一行人准备离开时,老乡的女儿叫住我,向我表白了心声,弄得我不知所措。
我叫赵志勇,63年生人,家住陕西榆林。在家里,我排行老大,下面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
小的时候,我吃尽了生活的苦,每当家里粮食不够吃,我就带着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荒山上挖野菜,要不然就是摘槐花。
我们把这些吃的拿回家里,母亲用清水洗干净,放在砧板上剁碎,然后放少许的玉米面或者高粱面,煮熟给大家充饥。
天天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,把我们兄妹几个吃的脸色蜡黄,长得和面条似的,一阵风刮来,都能把我们吹跑,特别是最小的妹妹,本来就是早产婴儿,体质差,有那么一段时间,以为她要挺不过去。
只有切身体会过那种挨饿的滋味,才能理解我所讲述的事实。
在我十五岁那年,老家这边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旱灾,从把种子播到土壤里,一直到秋收的季节,没有下过一场透雨,别说庄稼颗粒无收,就连人喝水都成了困难。
我们村百十来户人家,平时都是吃村东头那口井里的水,不过那一年,井干了,想要吃水,就得步行两公里,去隔壁村挑水回来。
那一年我刚初中毕业,本来要去县高中继续求学,不曾想被父亲拽回家里,让我帮助他和母亲一起扛起家庭的重担。
没办法,我是家里的长子,做出一点牺牲是人之常情。就这样,我天天跟着父母去生产队干活。
我在农村长大不假,但是起早贪黑地干活,我还是第一次尝试,第一天去上工,回到家里,我就趴在炕上起不来,连晚饭都没有吃。
我在屋里听到父亲给弟弟妹妹讲“你们几个要好学习,要不然就得像你大哥一样,一辈子当农民,没有出头之日。”
我听父亲这么说,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,打湿了枕头。
我在生产队干了大概大半年,大队书记决定办个村小,让我去当民办教师。
当时,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,不用去田间地头干活,而且还有现金补助拿,这种打着灯笼没处找的差事,不是谁都能摊上的。
我二爸是贫管会主任,也是村委会成员之一,当村里决定办村小时,我二爸就和大队书记商量好了,留一个民办教师名额给我。
那天,二爸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父亲时,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,甚至都被感动哭了,这个被他骂了半辈子的弟弟,关键时候还是有点用处的。
我们这个村小一共开设了四个班级,我教一年级、二年级,大队书记的儿子教三年级、四年级。
本来说好我教三、四年级,可是大队书记想证明自己知识渊博,执意要教高年级,可是教了大概两个月,他提出和我调换一下,原因很简单,有些题,他自己都不会。
人家父亲是大队书记,我本不想换,碍于他父亲的面子,不得不换。
在村小当老师期间,我的日子很清闲,每次在学校上半天课,下午名义上是去公社的学习班里上课,其实就是混日子,有时候上面老师在讲课,下面坐着的民办教师都打呼噜了。
自从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次走到乡间小路,乡亲们见到我,会热情的和我打招呼“赵老师,下班了。”“赵老师,今天没去公社学习呀?”
每次听到他们称呼我为赵老师,我很自豪,享受被他们恭维的话。
我当了一年半的民办教师,突然有一天,大队书记找我谈话,说让我当小学老师有点屈才了,他想帮我调到公社中学当老师。
我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,教小学没有压力,却是去了中学,肯定胜任不了。
我还是太天真了,大队书记说是让我去中学教书,实际是想安排他的侄女回村小当老师,可是碍于面子,他不好意思直接把我拿下去,所以才编造了一个不错的理由。
我很生气,想找大队书记理论一下,但是父亲把我拦在门口“儿子,胳膊拧不过大腿,和他唱反调,没有好下场。”
是呀,人家能干二十几年的大队书记,肯定有过人之处,不是我这个愣头青可以轻易扳倒的。
说来也巧,我刚不当民办教师,突然听到一个消息,部队来我们县上征兵了的,而且征兵指标比往年多了不少。
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有个从军梦,如今有机会实现,我必须要去试一试。
我去村支部找民兵连长要了报名表,填写完报上去没超过五天,就通知我去县武装部初审。
初审分为三部分,体能测试、身体检查、政审。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家里农活没少干,加上当民办教师期间,我偶尔给孩子们上体育课,所以体能测试、身体检查时,我是很顺利的通过了。
关于政审,我也不担心,家里世代为农,祖上也清清白白,一点污点儿没有,所以在走访环节,我没有过多担心。
1981年12月上旬,武装部把入伍通知书下发到村里,在我来到通知书时,兴奋的整夜没睡。
父亲或许是感应我没有睡着,他把我叫到一旁,非常耐心地叮嘱我“儿子,如今你有机会去当兵,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,别给你爸妈丢人。”
“爸,你放心吧,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父亲听到我这句承诺的话,什么都没有,拍了拍我的肩膀,转身离开了,那一刻,我能感觉到他哭了。
那年,全县有237应征入伍,分配到全国各个军区服役,而分配到新疆军区的只有三个人,一个是我,另外两个是二次入伍的老兵。
我们坐了将近50个小时的火车,终于来到所服役的军区。这里除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就是戈壁滩,十天半个月遇不到一个人。
初到这里,我水土不服,上吐下泻,去医务室拿了药,赶忙跑到厕所里蹲着。
很坦诚的说,那一刻,我后悔来当兵了,幻想过部队的艰苦,但是没想到这么艰苦,连最起码的水源都不能保证。
为了节约用水,我们洗漱完的水要用一个大水桶装着,沉淀好了,晚上用它洗脚。
我们这里比较艰苦,除了日常的训练,而且偶尔会出去巡逻,大家有说有笑,时间过了的很快。
在入伍的第二年,也就是1983年,连长和指导员把大家召集到一起,说抽出一个排战士去帮助老乡割麦子。
来这里一年多,还没有见过当地的老乡,大家都想去,我很荣幸被选中了。
我们早上五点坐上大卡车,中午12点才到达目的地。
我们找到要帮扶的对象,赶忙去田间地头干活。
战友们边唱着嘹亮的军歌边舞动手里的镰刀,没一会儿功夫,割了好大一片。
或许怕我们口渴,帮扶对象的女儿提着水壶过来给我们送水喝,在路上被一条疯狗拦住去路,她吓得哇哇大哭。
我和战友们听到哭声,都直起来了腰,望向哭声的方向。
凭直觉,应该是女孩遇到了危险,大家一起冲了过去。
我跑的最快,看到疯跑把女孩逼到角落里,随时要发动攻击,我带着镰刀就扑了上去。
我怎么可能是疯狗的对手,手臂上好几处都咬伤了,这时候战友们也赶到,大家一起将疯狗打死。
那一刻,我知道自己被疯狗咬伤,大概率会得狂犬病,所以知道自己要命不久矣了,不过,害怕老乡担心我的生命安慰,我还是强壮镇定,说自己啥事儿没有。
我因为被咬伤,指导员没有让我跟着他们去麦田割麦子,而是留在老乡家里养伤。
我们在老乡家里呆了三天半,临走的时候,老乡的女儿叫住我“赵同志,你是为了救我受伤的,要是出了意外,我会对你负责的。”
女孩说要之后,脸红到耳根处,战友们听了,更是起哄,直呼“嫁给他,嫁给他……”
“你不要有心理负担,我没事的,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。”我在老乡家里养病这几天,都是她照顾我,哪怕洗脸,都是她帮我。
我算是福大命大那种,被疯狗咬伤,竟然没有发作狂犬病,而且活的非常好。
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股票杠杆炒股,我有时候回想起那个女孩,不知道她如今是否还记得我。
大队疯狗赵志勇赵老师老乡发布于:天津市声明: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,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